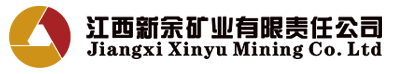
绿萝的藤影斜斜地爬上文档页眉,键盘敲出的字符便染了三分青碧。两年前的仲夏,我抱着资料箱穿过走廊,“闯”进党委工作部,桌旁那盆被盛夏阳光浇透的绿萝正垂下一茎新藤,像未落笔的破折号,悬在办公桌边缘,它成了我改稿时最忠实的“观众”。
还记得初涉企业宣传领域时,面对“技术攻关”“率先垂范”这些硬邦邦的词句,我总在材料堆里打转,字句如晒蔫的菜叶。“党员带头科技创新”“青年突击队攻克技术难关”……僵硬的表述常让鲜活的实践沦为晒干的标本,没有基层故事的温度。
前辈一语中的:“要善于总结学习党报党刊中的好写法、好文法,好文章要像绿萝,得往土里扎根。”渐渐地,从不断地学习揣摩中,我得以初窥文字应有的肌理。我试着把土地数字化管理系统比作“电子界碑”,用“劳模工作室的灯光”串联起技术攻关的深夜,把老党员的皱纹改成“平安建设的年轮”。可交稿前还是纠结着这样的比喻、用词是否准确而时常发愣,像捧着新陶坯的学徒,生怕手一抖就碎了。
绿萝的藤蔓在风中轻轻摇晃,像在替我忐忑。无数次,当我把素材的拓扑图转化为文字矩阵后,却常常对着预览界面患得患失——那些跳跃的小黑块写出了真情实感吗?倾注的心血能否得到领导的肯定?我会因发布的稿件一字未改而窃窃自喜,也会因被领导推倒重来而闷闷不乐。那些反复删改的段落,常让我羞愧——文字功底浅,对企业发展脉络摸不透。两年里,七百多次后台修改记录里,藏着无数笨拙的脚印。
直到某天在电站遇见年长的运维班长。他说,“看着公众号里你们把一次不到一个小时的抢修写出了花,我们电站的同事都很高兴。我工作几十年了,看来做了事还是得说出来,让人看到。”此刻,某种比点击量更厚重的成就感在心里抽枝。
我开始学会蹲下来看世界,用文字的视角扫描每个基层故事的温度。把运维员后背的汗渍调成渐变色阶,将警报声谱写成琴弦上的急板,让探照灯光斑在段落间流转成星轨。稿子里文字仍会撞见生涩的比喻,像错位的齿轮卡在段落间,但我不再忐忑,绿萝的根正在土壤缝隙里延伸,而我的笔尖已学会在修改中发芽。那些被红笔划掉的笨拙词句,终将成为藤蔓攀向下一寸晨光的台阶。
生长本就是修正的过程。绿萝的每片新叶都带着虫咬的缺痕,就像我的文字终究要在真实土壤里,慢慢长出自己的年轮。